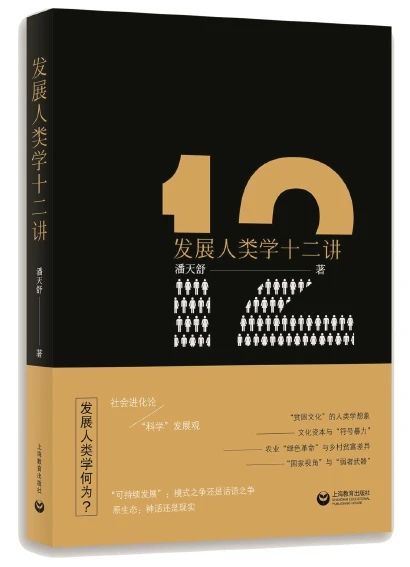编者按:2020年4月4日,《解放日版》“读书周刊”专栏刊发了记者夏斌对社政学院潘天舒教授的专访。在专访中,潘教授基于其新作《发展人类学十二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提出了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和实践目标、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发展人类学的存在方式等,并介绍了他的研究经历及其所主持的“上海研究”项目十几年来的进展。在此全文转载如下:

从“足不出户”的扶手椅模式、“浅尝辄止”的露台访谈,到以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田野调查阶段,人类学研究奋力摆脱“按图索骥”,一步步走向务实、有趣、有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社会进化论还有多少解释力?“原生态”与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面对“技术至上论”的冲击,人类学者在发展研究和实践中能够有何作为?
在《发展人类学十二讲》一书中,复旦大学教授潘天舒对几十位近现代人类学家的论述进行概括,对涉及人文、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焦点话题展开探索。这样的“温故”,是为了知新;这样的反思,是为了更好地从“心”出发。
难以独善其身
读书周刊:人类学者是不是都热衷于“走进田野”?
潘天舒:田野研究对于人类学者来说,就像档案研究之于历史学家、实验室研究之于生物学家那么重要。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田野调查始终是人类学者赖以生存的手段。这本身也是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和开放。
早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从旅行者、探险家等撰写的域外风情杂感或游记等二手报道中获取素材和灵感。这种在书斋或图书馆“闭门造车”的研究路径,被称为“扶手椅”工作模式。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启了“露台访谈式”工作模式。研究人员在住处的阳台上,与召集过来的当地人进行交谈,进而获取有价值的材料和信息。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真正专业的人类学者应该在选定的研究场所,如村庄、集镇或街区居住一年以上的时间,同研究对象共同生活,融入当地习俗并尽可能参加各种仪式和活动,力求获取有助于解决疑问的细节和信息。
这种以参与式观察法为标志的田野调查人类学,是费孝通当年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所创立和完善的。费孝通先后完成的广西花篮瑶研究、《江村经济》研究和民族识别研究,充分展示了人类学方法在经过调整和灵活使用后的巨大价值,为发展“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提供了范例。
读书周刊:对“细枝末节”的钻研,会不会让眼界变得狭窄?
潘天舒:确实,田野调查的地方性和对“细枝末节”的追求,某种程度上会使一些人类学者陷入特殊的地方情境而不能自拔。
《发展人类学十二讲》中提到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贫困文化”概念,就是人类学家刘易斯拿“文化”说事犯下的“无心之过”。这一在“狭窄”眼界中形成的田野发现,对国家层面福利政策的制定、修改,产生了不利于维护穷人福祉的后果。
读书周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潘天舒:作为学者,我们可以发挥文化批判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让自己获得一种将“细枝末节”与“宏大社会力量”相联系的能力,培养对个体经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敏锐反应。
作为普通人,我们的视线难免会局限在由家庭、亲朋好友和同事构成的微观世界里。“社会学的想象力”恰恰也能帮助人们摆脱“井蛙之见”,看到个体生命轨迹与社会事件的结合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到近来发生的美股连续熔断,都会对全球各地诸色人等产生影响。无论是一线的劳动者,还是华尔街的精英,都难以独善其身,都必须深深懂得何为“命运与共”。
读书周刊:近年来,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潮有所抬头。这会不会助长“文明冲突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成为可能?
潘天舒:“文明冲突论”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惊世之语”,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它将一种早已为人类学界唾弃的伪科学文化观搬上国际政治舞台,是出于维护意识形态的需要,是对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成果的视而不见。
“文明冲突论”的一大问题在于,它将“文化”看作某一文明中自成一体、一成不变且几近僵化的信仰传统和价值体系。这种对文化、文明随意贴标签的做法,对意欲寻求治学捷径的学者来说有一定的蛊惑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知名学者的演讲、辩论和论著中,“文明冲突论”常被引为立论依据,而不是质疑的对象。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只有以人类学、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成果来遏制“文明冲突论”造成的不良后果,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认识论支撑。
在“象牙塔”外生存
读书周刊:人类学总让人觉得高冷,似乎缺乏实用性?
潘天舒: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努力将学术研究的热忱付诸改造世界的行动之中,从而让“针对发展的人类学”既保持人文情怀,又能够接上地气,避免陷入后现代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
例如,《发展人类学十二讲》重点关注了金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个例子。金墉是一名对经济增长保持质疑态度的人类学者和医生,却有机会主导一个以促进发展为使命的国际组织。这一“小概率事件”足以激励发展人类学者超越经院藩篱,将批判意识转化为实干的专业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定义自身的角色和作用。
读书周刊: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人类学者持何种立场?
潘天舒:在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发展人类学主要有两种存在方式——
第一种是以应用实践为导向,通过发挥人类学的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等方式,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
与此相伴,以参与式观察为标志的田野工作法日益普及,从而使发展人类学更像一门应用学科,得以在“象牙塔”外生存下来。经过这种专业训练的人,在对问题进行观测、诊断时,具有不同于经济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视域。
第二种存在方式就是依托高等院校的教研平台,以反思和批判为导向进行学理探讨,主要致力于对发展理论、过程和实践进行质疑和反思。
读书周刊:这两种方式有何实际价值?
潘天舒:面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这两种存在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和价值。譬如,在国际发展实践中,得天独厚的整体论视角让人类学家几乎一眼就洞穿症结:早期国际组织资助的经济援助项目之所以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根本原因在于项目设计者和执行人笃信“技术至上论”,对项目实施地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不是一知半解,就是视而不见。
从雪地摩托对萨米人(主要分布于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的北极地区,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兴土木对原住民生存环境的冲击,到盲目推广婴儿配方奶粉所造成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可以看到,发展人类学者的诸多洞见,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把握适应性、整合性、可塑性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但要警惕的是,如果说国际组织在向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援助时,喜欢加上诸如接受市场经济模式、改革传统价值体系等先决条件的话,发展人类学者则应避免走向另一极端——要求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维持现状、固守“传统”,甚至不惜以压制革新为代价。
聚焦疾病与贫穷
读书周刊:人类社会的两大夙愿——消灭疾病、消灭贫穷,是否也是发展人类学的关注重点?
潘天舒:消灭疾病、消灭贫穷是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和实践目标。
在此前的一些经济学家眼中,以渔猎为生的原始人多半过着食不果腹乃至饥寒交迫的日子。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提出,在渔猎采集社会,多数人的工作时间比现代化大都市的上班族要短,劳动强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有闲暇时光来交友、娱乐。
《石器时代经济学》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原始人群没有什么财产,但他们并不贫穷。贫穷既不是微不足道的物品数量,也不只是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断章取义地看这段话,也许会觉得这是一种美妙的想象——前工业化时代的人远离尔虞我诈的市场社会,生活在不受钱财困扰的桃源仙境。其实,此段论述表达的不是怀旧情感,而是一种深邃的历史洞见。它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反思困扰人类社会的诸多发展问题打开了新通道。
事实上,消灭疾病、消灭贫穷或者说社会的健康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财富的积累,而需要对传统的社会进化论、经济增长阶段论、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展开重新审视。
读书周刊: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与瘟疫作斗争。当前要形成抗疫合力,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潘天舒:近20年以来,针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包括SARS、禽流感、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和至今尚未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国造成了多方位冲击。这已远远超出了病毒学、流行病学、公共健康和公共政策领域的认知范围。
基于这一态势,有必要进行实时实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充分发挥人类学、民族学的想象力和民族志方法的洞察力。在这方面,哈佛大学人类学者凯博文和华琛的研究值得重视。
例如,凯博文针对“疾病污名化”和“社会苦痛”体验的阐述,华琛对“前现代”食物生产体系与“后现代”生活方式共存而产生的风险、挑战作出的预判,都可以为应对和研究此次疫情开启思路。
政府和社区有必要集众多学科之所长,对复杂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探讨,以做到未雨绸缪。其中,医学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的桥梁,一方面连接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面连接健康和政策科学,可以为案例研究和找寻潜在的有效干预方式提供视角、思路和途径。
同时,来自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心理治疗领域的专家应与工程、农业、规划和技术部门的专家进行合作。为应对灾难而组成的规划团队中,还应当包括非政府组织人员和社区一线代表,等等。
空间重构下的挑战
读书周刊:国外的人类学者不少有社会学、经济学背景,您却是从文学转过来的,是什么机缘促成跨学科的?
潘天舒:我是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当时,复旦外语系对考生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除了雄厚的师资之外,还有在大三时去英国利兹大学学习这一“诱饵”。
在利兹大学交流学习的一年,是我从文学转向人类学的一大动因。在那里,拿到英语系教授开的书单,我们真正开始接触以阅读原典为特色的英国文学专业训练。这与国内大学英语专业的教学模式差异显著。长长的书单列了从米尔顿、莎士比亚、艾略特、伍尔芙到玄学派诗人等风格各异的作品。
现在想起来,文本带来的“文化冲击”远远没有语境来得深刻。上世纪80年代,英国作为一个“他者”,留给国人的印象基本上是狄更斯时代的“雾都”。但当我到了利兹这个正在复兴的英国北方工业城市时,领略了一番不同的景象。同时,从文化差异引起的误会和歧视中,我进一步体会到了“族裔中心主义”的可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功用及其局限。
毕业那一年,我还没想清楚到底要从事什么工作,就先去上海郊区支教一年,然后,留校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的协调和翻译工作,这让我有机会与国外来访的一流学者面对面交流。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校长谢希德主持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牵头开了一次跨学科国际会议,探讨上海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扮演的角色。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裴宜理(现在哈佛)等在内的一批中生代学者全都来了。
我除了翻译会议论文之外,还为美国人口学家李中清(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的发言作“同声传译”。李中清采用清朝某王爷府添丁、秋收的第一手材料,试图通过对历史统计数据的重新检视和解释,来探讨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变化、农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令人大开眼界,也让我萌生了继续出国深造的念头。
读书周刊:“喝洋墨水”的经历,让您有新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介绍上海。2007年出版的英文专著《邻里上海》与今天的《发展人类学十二讲》有什么联系?
潘天舒:《邻里上海》通过对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的地区档案的发掘利用、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口述史记录,通过深入社区基层的观察、探访和话语文本分析等,对上海普通居民、社区干部和基层官员的心路历程展开了系统梳理。它的一个特点是,在田野描述、事件重构和分析过程中运用“历时”与“共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见微知著。
比较来看,《邻里上海》是基于社区研究的都市民族志作品,《发展人类学十二讲》是旨在推介、评述一门有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的分支学科论著。
读书周刊:十几年过去了,您的“上海研究”有什么新进展?
潘天舒:这些年来,城市空间的重构以及社区建设重心的转变,特别是“熟人社会”基本不复存在,对继续从事历史记忆、地方感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2006年归国之后,我更多走向跨学科的团队课题研究。我所在的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在儿童与青少年心理问题、适老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跨界合作,逐步确立了以医学人文和全球健康、城市社区民族志研究和发展人类学的教研方向。这可以为推动人类学研究更具前瞻性、植根性、公共性打下扎实基础。